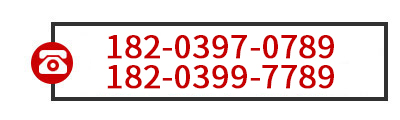数字技术的广泛应用产生了“数实相融”的新型治理情境,导致“上下共治”这一新型治理模式出现,超出了已有理论的解释边界。
“上下共治”治理模式的出现,表明数字时代改变了“行政发包制”“上下分治的治理体制”“国家治理的制度逻辑”等理论的前提预设。第一,“数实相融”的新型治理情境对“行政发包”的成本压力和质量压力这两个约束条件都有所改变。一是凸显了基层政府的数字信息劣势和属地原则效能衰减的问题,导致“行政发包”的成本压力(基层政府信息收集和责任界定的成本压力)大幅度的增加;二是凸显了社会风险的规模放大效应,导致“行政发包”的质量压力(下级政府行为有偏时的风险规模)大幅度的增加。这两个条件的改变都使得上级政府有必要直接参与治理,以降低整体的信息收集成本和风险压力。第二,“数实相融”的新型治理情境冲击了风险可依据属地边界进行分割的预设,可能同时涉及全国性和地方性公共事务,导致局部对全局的影响变大,社会风险的规模放大效应凸显,使得“上下分治”的治理模式出现失灵,只有“上下共治”才能应对“数实相融”的新型治理情境。第三,“数实相融”的新型治理情境冲击了基层政府具备信息优势与有效治理能力的预设,即仅仅依靠自上而下的行政分权并不能确保基层政府具备有效治理能力,而是需要上级政府更直接的治理参与;修订了上级政府缺乏信息优势故而主要通过动员式治理等方式应对组织危机的假定,凸显了数字时代上级政府应对下级政府行为偏离失控的新方案,即开展线上治理和风险监测预警等的常态化治理机制。
如表2所示,我们对五种治理模式作比较。既有国家治理理论的共同特点在于,都是以实体空间的属地化分级治理为经验基础,提出的“行政发包”“上下分治”“垂直管理”“高度关联”等概念都旨在刻画多层级政府应对实体空间治理问题所发展出的治理模式。其中,“行政发包”主要应对激励问题,有助于降低中央政府的组织成本;“上下分治”主要应对风险问题,有助于将风险分散在局部、隔离和化解在基层;“垂直管理”主要应对地方干预问题,有助于实现一体化治理、维护中央政府利益;“高度关联”应对组织危机问题,有助于对地方政府行为进行纠偏。进入数字时代,这四种治理模式并未失效,而是稳定存在,它们涉及的治理问题依然存在,依然具有难以替代的功能。然而,“数实相融”的新型治理情境对基于实体空间的属地化分级治理构成基础性挑战,急需具备适应性的新型治理模式才能实现有效治理。基于此,“上下共治”作为一种新型治理模式出现了,通过上层治“数”、下层治“实”、分工协作和共同治理来应对新型治理情境,弥补基层政府在数字信息、线上治理、跨区域协调和风险监测预警等方面的短板。
“上下共治”治理模式体现出来的政府治理变革逻辑在于:为了应对“数实相融”的新型治理情境,多层级政府的关系属性、实际角色和运行方式在“行政发包”“上下分治”治理模式的基础上出现了三个标识性和实质性的变化。一是中央政府和省市政府愈发凸显地直接开展数字信息收集、数字空间治理(风险监测预警)、跨区域事务协调等;二是中央政府、省市政府、县乡政府之间的优势互补、分工协作和共同治理效应更加凸显;三是中央政府和省市政府对于治理过程的控制性、整合性、协调性和监督性在增强。正是因为这一变革逻辑,“上下共治”既有别于“行政发包”“上下分治”,又与它们有一些相似之处(如实体空间属地治理任务的层层分解)。也正是基于这一变革逻辑,在“上下共治”治理模式中,虽然中央政府和省市政府保留关键权力、直接参与治理,但明显不同于“垂直管理”模式中的一体化管理和“高度关联”模式中的集中式动员。因此,“上下共治”是一种新型治理模式,是多层级政府应对数字时代环境巨变的适应性变动,这种变动是渐进性而非颠覆性的。至此,能得出一个推论,即在其他条件(如垂直管理成本)相同的情况下,如果一个领域的线上化、跨域化、风险性程度越高,那么多层级政府呈现“上下共治”治理模式的可能性越高。
值得指出的是,在当代中国国家治理体系的整体结构中,“上下共治”与“行政发包”“上下分治”“垂直管理”“高度关联”之间并不是竞争和替代关系。第一,五种治理模式之间有互补和并列的关系。它们是多层级政府面对不同环境压力、应对不同治理问题、采取不同应对策略而生成的不同治理模式,共存于数字时代中国政府治理的实际运行中,只不过分布于不同的治理领域、治理情境或治理阶段,发挥着各自不同的治理效能,在中国国家治理体系中扮演不一样角色而已。第二,五种治理模式并非基于单一的维度划分,而可以从不同维度进行分类和比较。例如,相比“高度关联”而言,其他四种治理模式是更加常规型的治理模式;从地方分权程度看,“行政发包”“上下分治”更高,“垂直管理”“高度关联”更低,“上下共治”居中;从中央政府或省市政府的过程控制程度看,“行政发包”“上下分治”最低,“上下共治”较高,“垂直管理”“高度关联”更高。第三,五种治理模式并不互斥。例如,“行政发包”中内含“上下分治”,“上下共治”中包含“上层治官”和“不完全发包”,“垂直管理”“高度关联”中也可以存在“上层治数、下层治实”。
与前数字时代的四种治理模式不同,“上下共治”治理模式的生成和运行,反映出当代中国国家治理深层制度结构中的一些新变化。第一,“上下共治”映射出正在发生深刻变化的当代中国政府治理理念,即更强调复杂性、系统性和协同性的治理理念。第二,“上下共治”反映出多层级政府在数字空间的治理权结构特征。数字空间治理权(特别是数据权)虽然在法律上尚缺乏完整和明确的界定,但理论和实际上的最终控制权都属于中央政府。从各领域多层级政府的实际运行看,数据权自上而下依次递减,构成“信息优势的上下分化”的关键制度基础。不同国家的体制背景不同,可能带来不同的数据权结构,进而影响信息优势结构的差异。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上下共治”治理模式可能蕴含着一定的本土特色。
那么,新治理理念将如何进一步引领数字时代的政府治理变革?新的治理权结构是不是会稳定存在,有几率发生何种变化?如何更加全面和准确地理解数字社会持续健康发展与当代中国政府治理变革之间的关系,如何从国际比较视野出发把握中国政府治理变革的特点,还需要更加多、更深入的研究。
作者向静林,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副研究员(北京100732);艾云,中央财经大学社会与心理学院副教授(北京100081)。